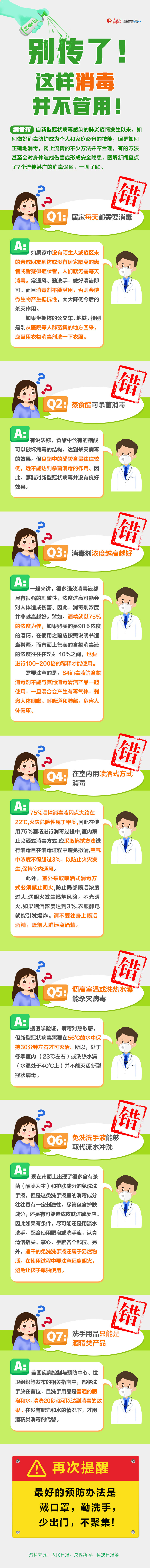除了这些自觉以本土身份去发声和互动的一些人之外,我们会发现,东北意识逐渐出现在了一些并没给自己贴上本土标签者的身上。我想举出一个案例,就是所谓的“彪学”、老舅以及他们跟下岗创伤的间接关系。
彪学,顾名思义来自《马大帅》电视剧里头的角色范德彪,女主人公的老舅。最近两年来,b站上有很多up主去做剪辑,把马大帅的也就是范伟的表演影像跟其他的影视剧或者是音乐结合进行二创。这种剪裁有一个基础:《马大帅》这个电视剧是在东北2000年到2012年短暂的繁荣期里拍摄的作品。《马大帅3》中刘能演的刘总在跟赵本山的对话中明确说到,他的前老丈人是工厂的厂长,后来他把工厂盘了下来,所以才发的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赵本山好像完全代表着一个乡土的世界,他跟东北的下岗工人的、城市的世界是分割的,但其实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在马大帅这样的一个文本中,本身我们能找到很多的体制改革的痕迹,我们能看到下岗潮大量造就的城市游民,包括四马路钢子的这么一个形象。钢子和他的小弟们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东北“业余”黑社会的形象,它是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或者后单位制阵痛的体现,恰恰是由下岗直接造就的。再比如说这里头阿薇这个角色,她明确讲过,自己原来是在市宾馆上班,后来就到维多利亚了,那市宾馆怎么样了,是不是黄了?这种剧本之外的潜文本其实有很多改革伤痕的留白。

马大帅的摄影之一是张猛,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大家应该都看过的《钢的琴》,但我觉得他的第一部电影《耳朵大有福》同样也很好,同样是由范伟来饰演一个“内退”的铁路工人。说是内退,其实就是下岗对吧?因为在体制改革的后期很多地方不敢直接下岗就搞内退,工人没到岁数就从工厂里赶出去。实际上,通过张猛这样的导演或者是范伟这样的演员,我们发现在赵本山作品的文本内外,实际上东北的文化世界本身是没有那么割裂的,这也是之前我们说的,把东北的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认为东北就是乡村的这些人,他们普遍不能理解东北文化本身具有主体性,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移民到关内或者是认可关内的东北污名化,所以他们拿原来用来骂乡下人土老帽的老倒子这词,来指代现在不认可东北的这些人,这样的一个建构和叙事本身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在我们分析完这些文本的外部之后,我们来讨论其中一个剪辑者叫做“德彪的奇妙冒险” 。他的特点是剪辑了很多香港或者是日本的老电影,把老电影的叙事节奏和台词跟马大帅的表演结合在一起。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评论群下面的这样一些对话。
首先,你会发现他的所剪辑的这些文本的下面,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常见的、对东北的污名化的叙事,比如说他有一次剪了一个1960年代的老电影《林海雪原》,他在发布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我的爷爷长得很像杨子荣”,然后下面最高赞的几个评论说:“座山雕你还搁这看视频呢,你窝都被端了。”“座山雕你来长白山指定没你好果子吃,狗皮帽子给你拽掉,必须打你脸。”“三天之内活捉你,百鸡宴都给你扬咯”。大家都明白这个东西显然是在戏仿快手上的那种东北土味视频,虽然他主观上没有那么大的恶意,但是客观上显然是一种对东北的污名化和东方主义凝视对吧?有些人会拿这样的一些话术去代表东北,甚至认为这样一种当代东北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凝视下形成的自我形象,可以被倒推回60年代在东北发生的红色经典的影片里,这些人在这里明显是一种对东北的持续俯视,是想用今天东北的他者形象与改写红色经典中作为“主流文化”承担者的东北形象。但同样的视频下面另外的热门回复,是这样讲的:“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清末明初大量移民的涌入,加上黑土地的原始富饶,使得其人民具有别于关内人的一股冒险的气质。无论是闯关东,还是张大帅的发家史,还是解放后剿匪及工业化建设,这些都是构成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气质的来源。马大帅具有的魔幻现实主义气质,就是来源于此。这次《林海雪原》看得出up主是用心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我觉得很好。”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看出在这类视频中,看热闹的人看到的是东北文化对于香港电影为代表的经典文化的戏仿(从作者将马大帅图像与港片叙事及声音结合的努力中),看到的是东北地区这么一种污名化的、自我东方主义的形象的再生产,比如说社会人、喜爱暴力,比如说夸诞虚饰、常发出人身威胁的形象,比如说不务正业的、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一些东北人来说,他们在up主的同一形式的剪裁中,看到的却是东北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可与港台相比的现代性风景,是主体性的重新浮现。这一类视频正是印度的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提出这样通过模拟和杂糅后形成的“第三空间”。香港所代表的现代性和霸权,在这样的一种“第三空间””中,成为东北确认自身曾经有过现代性的抓手。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频精确地看到,同样的一种文化产品,对于他者和对于东北人自身来说,意义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2018年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观察东北直男报告》里头把东北的人描述成是衰落的、没有道德感的。当时有人针对这个文本提出了批评,他批评东北人的地域自黑:“东北人不会去主动利用东北话语改造自身的身边的权力关系,他们只是让看客满意而已。”在这点上就跟其他的一些地方主义者做的类似的书写完全不同。比如前几年很火的一个藏族自媒体写手扬卡洛夫,扬卡洛夫反复写女文青西藏的这个命题。我们之前引用的这个批评指出,在扬卡洛夫的叙事里,“康巴汉子们可以通过主动迎合这些女文青的东方主义想象来获得性满足,以这种自我的东方主义为代价,康巴汉子们得以改写了文本中所叙述事件的权力关系,看似懵懂的被动者成为了主动者。这样的一种描写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是因为康巴汉子作为一种身份是被康巴人或者藏族人所认同的,依赖着某种自觉的身份意识,他们能够在这种后殖民语境的、东方主义凝视的叙事中,倒转这种权力关系,获得某种主动性。东北人过去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东北人缺少能够与藏族意识相比拟的东北意识。”
但是现在,在“德彪的奇妙冒险”这么一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人已经能够同样地利用这种他者的凝视反转权力关系,尽管这种反转是有限的。
这一点我们将马上用另外一个文本来说明去年火遍全国的《野狼Disco》。《野狼Disco》这个文本同样涉及到东北历史,就是我一开始讲过的,东北经济在近三十年经历了两重波浪的曲线变化,而不是像我们大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这么一个直线的下滑。它这里指涉了三重东北。
第一重是迪厅和霹雳舞涌现的八九十年代的东北,就是作为历史记忆的东北。刚才我们讲到过,在这个时期,东北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出现了畸形繁荣,企业不用再为长期的全国计划负责,而可以将更多的原本的再生产基金,如研发经费、储备金、设备折旧费等倾斜于商品生产,占领地方资产,在全民消费缺口大开的时代赚取了丰厚的业绩,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依赖于企业中一长制的回归和企业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瓦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由集权带来的腐败日益增长,收益都收入私囊。然而好景不长,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商品经济无法摆脱的魔咒。到了八十年代末,价格闯关失败,地方市场饱和,很多企业遭遇库存危机,面对产能过剩的局面,企业又不能合法裁员,因此只能缩短职工劳动时间,以假代薪。因此,在年轻工人子弟这些东北人眼中,福利挺好,因为寅吃卯粮;又不用操心工厂事务,因为你失去了管理权;又充满闲暇时光,因为缩短劳动时间又不用担心下岗。出现了一个虚假的黄金时代。董宝石本人也属于这样一代人。
如今回望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一诞生就指向了彻底的毁灭,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中,因为大家都饿不死,然后又有一些闲暇时间,所以在前三十年延续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瓦解之后,东北人在文化交流中构建出了一个新的东北,也就是作为文化消费品的东北。
在80年代的时候,与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这一符号遭遇边缘化。从80年代的东北电影制片评书题材和文学写作转向中可以窥见一斑东北人以往最擅长扮演的劳动模范,或者是全国的工人阶级身份的这样一个典范形象的这种身份不灵了。但是东北毕竟是当时全国性的底子雄厚,市民社会庞大的地区,有钱有闲的第二代东北市民,也就是这些国企工人,率先抓住了传入内地的欧美港台流行文化,并乐此不疲的参与其中。歌舞厅、录像厅、书报亭成为人潮涌动的地方。
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像董宝石这样的迪斯科或者是早期收藏爱好者在东北汇聚成流。刚才聊天里有人说这是一个李焕英的黄金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容是很准确的。虽然李焕英是在三线厂,不在东北本地。
第三重是在东北经济瓦解,流动的东北人在身份迷失中重新构建的东北,也就是作为认同符号的东北。经过90年代末的攻坚和21世纪末的混改,黄金时代轰然倒塌。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大下岗带来的是东北的经济动能丧失,市民社会瓦解,文化进一步受到贬低。很多的东北人,第三代东北人背井离乡到新的发达地区安身立命,讽刺的是,他们的父辈很大程度上用白条和倒卖成就了这种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
这一批流浪的东北人很大程度上不了解此前的历史,但又的确生活在这种历史效果之中。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家乡并不贫穷,却低迷颓废,关内人并没有在文化上比家乡发达很多,甚至还有落差,譬如在劳动保护、女性地位、社会互助和艺术欣赏等方面,但自己却必须要顺从某种隐形的凝视,承认自己来自观念落后的地区,必须接受开朗大方、喜欢台面、喜欢面子、善于表演喜剧等等莫名其妙的人设,才能够最快地融入发达地区经营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本土的东北人,他们也无法回到前两代自立自信的东北,成为了一些跑不掉的流浪者。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宝石等人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新坐标,为流浪一代的东北人构建一种最低限度注意,是最低限度的主体性。就是家乡的老舅,这是一位落魄的贵族。他告诉这些外甥们,那些凝视你的文明人,玩的都是你舅年轻时剩下的冷饭,外甥们你们不要怕,你们跟得上,有文化,他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年轻时都玩过。这无论是不是一种阿Q式的反抗,但具有镇痛的作用。
此外,这样一种来自长辈,恰好又是最年轻、最亲和的长辈的苦,事实上艺术地纹饰了第二代东北人真真切切的失败,又导致作为流浪一代的这一代东北人要与父辈达成某种和解。但是蹦迪总不能当饭吃,黄金时代以来种种不文明的经济、权力和地域文化的关系,怎么能在歌声舞影中得到超越和扬弃呢?这样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主体性,实际上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站起来的主体性,而只是某种“跪着造反”的这么一种姿态。
说到这里,我们说回那部最著名的描述东北的电影《钢的琴》,电影里面王千源在一条河里炸鱼,有人在知乎上问王千源炸的那条河在鞍山的什么地方。有人贴出了一张照片说,现在那条河已经变成了一个景观绿带了,那条河现在已经被整治,两边都是绿化带,非常漂亮。
那么,这一方面说明东北的衰落不是一个在所谓工业废土或者废墟里直接完成的衰落,它最后的彻底的没落恰恰就是在这条绿化带那样的景观空间里,而不是在蒸汽朋克的工业废土里。阜新的矿坑已经变成了国家矿山公园。沈阳铁西的旧城改造拿了联合国人居奖,而恰恰是这样的一些改造,这样的一些引进外来资本的操作,才真正决定了东北的命运。
是这种去工业化,和文化上的这种把旧有的盈利组织和工厂单位制的市民社会的打碎,决定了从单位制到后单位制再到东北失去了整个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就像我们反复所强调的这样,造成东北衰落的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持续的旧有的计划体制和人性,不如说是反复折腾的改革过程本身。
刚才我们讲过,李文亮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这个诗歌本身从艺术上来说不是特别优秀,但是最好的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向南的列车上载满了物资,这些物资是什么呢,就是工人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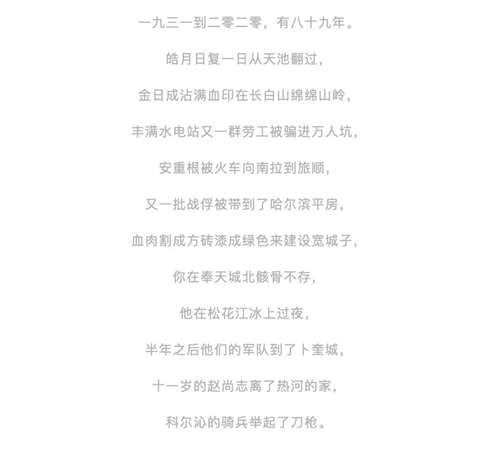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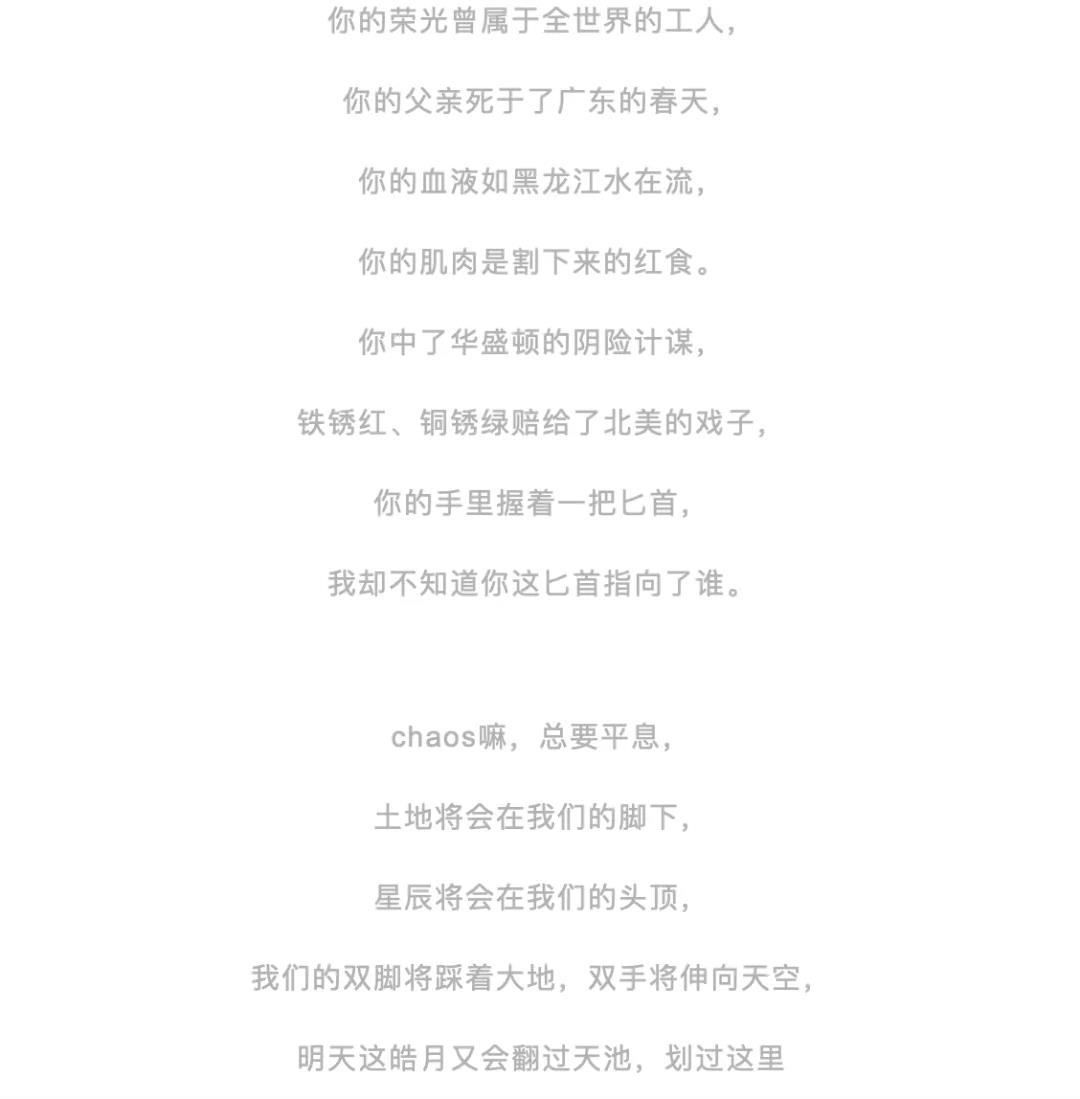
这两首诗歌,一方面,它们扎根于某种东北本土的想象,用了非常多东北本土的意象,尤其是第二首诗。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问题又显然不仅仅是东北这一个地方的问题,第一首诗可以作为第二首诗的一个补充,第二首诗强调了东北的问题的特殊性,第一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不仅是东北地区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历史,最后这个问题的出口是一样的在向南的列车上载满了物资,那就是工人的儿子。
接下来我向大家推荐b站上两个视频剪辑,第一个视频叫做《杀死那个东北人》(链接:/BV1b5411t7fY)。up主在投稿的时候写了一行说明:时代变迁,假药贩子最终把下岗工人掀翻在地。这个视频里除了一开场用了黄宏的那个著名小品,就是“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想所有东北人都知道这个小品。黄宏在讲了这句话之后,使劲地按下自行车打气筒,结果自行车的内胎爆了。除了这一幕之外,后面全部都是《钢的琴》这个电影的内容,然后配着《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歌曲。这个视频的弹幕非常多,弹幕里基本上都是某某厂,某某高中在此,比如说沈阳第一机床厂在此、齐齐哈尔重型厂在此、鞍钢第几冶炼厂在此这些是岁数大一点的人(的弹幕内容),还有一批人讲的是某某高中,比如说东北师大附中在这、哈三中在这、哈九中在这、省实验在这、辽宁省实验在这、本溪高中在这等等。
当然,这其实有同构性,就是东北曾经能够提供的是某某厂生产的产品,那现在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们剩下的就是某某高中,这些高中就是当年的厂矿,这就是东北给内地能提供的最后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视频的题目跟上一个非常接近,叫《杀死那个东三省人》(链接:/BV1CJ411X7C2),跟刚才那个《杀死那个东北人》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视频更好,因为它里头涉及到东北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不只是《钢的琴》。然后它结尾的电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由张猛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由范伟主演的《耳朵大有福》,铁路工人老范在空无一人的深夜街道上骑着自行车高歌《长征组歌》,是这样的一个结尾。这里再次暗示,东北的命运不只是地域问题,而更是后革命语境中的问题。

在这两个视频下面,有大量的关于下岗和东北生活的一些讨论,但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讨论。其中一个人就讲:“这几年东北的地域文化不再是赵本山和重工业了,出现了蒸汽波、赛博朋克等全新风格,虽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但是再过几年总会有新的文化拼杀出来的。希望能创造出类似成都的存在感很强的新文化。”这是他对东北的地方文化抱有了某种期望。
大家能看出来,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网络平台上的东北本土言说,我的态度多数是“理解但不认同”,我批评其中许多话术和它们自以为的对立面其实共享了一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在第五节中,我认为许多未必用“本土”相标榜的言说,尤其是一些二次创作品,倒是回应了东北更真切的问题。我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个人认为,东北的地方意识在什么意义上可能有正面意义,以及为实现这种正面意义,可能有怎样的出路。
我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时间的空间化这一个趋势,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线性进步的时间序列,在现代化的尺度上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在最近这十几年到二十年间出现了一个变化,时间被铺平在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经常说某一个地区代表着现代化的最高程度,而其他的地区跟这样的现代化先进的地区之间有多少年的距离。这样的时间的空间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症候,就是在被认定的所谓落后地区,本地人在反驳对该地这种落后现象的描述时,往往要强调说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而在向往先进地区时,也会同样以时间尺度畅想,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以达到如此。
这样的一种话术在东北存在一个颠倒的应用。刚才我讲过,在别的地方存在着一种线性的进步,但在东北存在一种线性的堕落。在时间的空间化语境中,东北自然就成为了空间中最落后的、作为一个绝对他者的象征。那么,我们凡是遇到中国的社会问题,你就会说像东北这样一个地区代表着中国整个体制的包袱,整个体制的弊病,那另外一些相应的地方就代表着中国体制的未来、中国体制的进步。
在这种意义上,东北在体制上和文化上被建构成了正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理想的“中国”的绝对他者。但这个绝对他者又不是作为一种全面对立的一个迹象出现,而是通过“相似,但绝不是”的一种方式出现。什么意思呢?就是东北很像中国其他地方,具有中国其他地方所具有的所有弊病,但恰恰是因为像,因为某种惰性,所以它又绝对不是。不仅是在制度上是这样,而且在语言上或者是文化现象上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rap,有个节目叫中国有嘻哈嘛;rap和说唱被建构成一种舶来自美国的最新文化产品,好像中国应该也学会。但对于东北来说,你只有喊麦,喊麦就是说唱的绝对他者。第一,他像说唱,它是一种对说唱的戏仿。但第二,它绝对不可能成为说唱,它一定是一种劣化的仿品,亦步亦趋,但泾渭分明。
再比如说,甚至连东北方言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家常说东北话很像普通话,或者说东北人觉得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东北人觉得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这件事情有毛病吗?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对东北口音的反讽,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东北人说的可不就是普通话吗?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语言学上的差距,本来就非常小,且互为连续变体。在这样的语境下,东北话恰恰是因为特别像普通话,所以绝对不可能成为(普通话)。你可以想象有些地区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同,有某种中介口音。比如我们说湖南有朔普,广东有粤普,四川有川普,但有没有东北普通话这个东西?没有,只有东北话。恰恰是因为接近,它才会被建构成一种绝对的他者。
在具体语言特点上来分析,实际上东北话也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内被建构成的一种作为普通话外部的喜剧语言、表演语言和舞台语言。不是任何语音学或者语言学的特点,而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上,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东北话才被建构成他者。所以你再拼命地讲接近东北话普通话的口音,人家也会根据细微的差别,试图把你的东北味儿识别出来,这根据的不是语言学的特点,而是某种气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听听长影在五六十年代的译制片配音,再把它们和近年“欢乐喜剧人”里的东北话比较一下就懂了。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可以说东北话识别术,在当代的某种反东北意识形态里发挥了颅相学在反犹主义中类似的作用。就像颅相学绝对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区别一个犹太人的头骨和雅利安人的头骨到底有什么区别,但你就是可以用它去识别谁是犹太人。东北人也是一样的,你其实很难去识别北方人讲普通话的时候到底谁在讲普通话,但是你认定你有能力识别出谁是东北人,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我们看到一个视频里面在打架、斗殴或者是争吵,然后说这人肯定是东北人,最后证实他不是东北人,是别的北方地区的人,甚至是南方人在讲普通话,只不过因为他具有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特点,而不是自然上的语音上的特点比如说声音大、看起来很粗暴,就把他识别为东北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北方言、东北人、东北文化,同样都是作为部分意识形态中,理想中国文化的某种绝对外部他者而存在。
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东北其实不存在,它只是伴随着整个东南沿海所象征的现代化话语诞生的幻像,或者说是现代化话语为了认识自身才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这个问题下,为什么我们认为东北人的存在是必要的,或者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只有在东北人并不存在的意义上,东北人的存在才可能有它的进步意义。
东北和关内的关系不是巴伐利亚和德国的关系,而更接近东德和西德的关系。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再见列宁》。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它说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事实是:被认为是完全出自于政治宣传的荒谬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在社会主义德意志灭亡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竟然真的存在。男主人公在和他生在西德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对话中,他的弟弟问他说你来自哪儿,男主人公说“另一个国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辩证法,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辩证法。他嘲笑的就是他创造的无论是新的共同体还是反抗他的运动。
所以说,一方面来说东北和所有中国的别的地区一样,处在一种类似的问题式里,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个别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可替代中心之外,大家都在陷入某种边缘化的状态中,陷入一种回不去的故乡和留不下的北上广的之间的夹缝的焦虑中,对吧?
除了这样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式之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东北曾经是原有的,前三十年用西方学者所说的、汪晖本人曾引用的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另类现代性、计划经济的现代性的这么一种模式的典范,恰恰是因为东北曾经是一种主流模式的典范本身。
因此东北作为一个他者,是被彻底建构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内部的绝对的他者。永远“有那味儿了”,但永远不可能是真的。东北被识别成是一个永恒的李逵身旁的李鬼。因此,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是不可能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完全彻底吸纳的。即使多数东北人曾经主观上或许最期待被吸纳,因为东北文化是主流文化的自身打造的一个影子和反题。因为像,所以绝对不是。和那种拥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所设想的“理想中国”的形象正相反,东北正是现实的中国,是少数全球资本主义的可替代中心之外的中国的代表。
在当代中国,区域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交织在一起,为政治经济中心区的少数人群赋予了一种标准的中华民族身份。而在广袤的中国腹地的众多人群,可能会被认为是只享有劣化版的民族身份。
这种方言政治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拜物化了的阶级身份表达。所以说,归根到底,东北的问题不可能在中国的问题得到解决前得到解决。我们不可能设想说可以通过重新地识别出一种东北的本地的身份,和靠着东北土地的丰富物产,实现一种东北人的这种所谓获得主体性的解放,我们只能期待着整个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发生某种变革,才有可能给像东北这样的一个内部他者带来某种声音。如果对东北身份的认同,走向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想象,那么,它将和今天东亚现存的任何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一样,不可能起到进步的作用。事实上,像上一节里我推荐的一些剪辑的短视频作品以及类似作品下面,就不难找到一些这样的留言:“我华北的,但同样体会到了悲哀”、“甘肃的工业城市有同样的感受”“南方矿冶小城相差不多”,以至于:“或许到最后我们的故乡都钝化得无法分辨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恰恰是“东北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决定了“东北人”应该存在。这是一种动态的、生成中的、拒绝凝固的认同,其目的绝非重新划定共同体的边界,而恰恰是抵抗那些试图在共同体中划界,建立差序格局的倾向。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恰恰是因为东北人是不存在的,决定了东北人必须存在。
东北人的存在和觉醒,本身成为爆破这种现代化的线性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不考虑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只考虑所谓的片面的发展的一些经济关系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抓手。所以在这个语境下,东北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东北人,对于整个中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最后,有那么一个bot叫做“外省文艺bot”,它在成立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创刊宣言,这个宣言里最后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
近年来发生在文艺空间的两种潮流,更加促成了“外省文艺bot”的成立。一是华北、中原地区出现了诸多以描写北方重工业城市的衰落以及县城、农村的生活记忆为主要内容的文艺作品,并且风靡一时;二是如今正流行的,由《野狼disco》所带动的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像华北、中原地区的这些文艺活动,以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虽然同时也为新的猎奇与营销提供了可趁之机,但它仍是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标志着本地人民的自觉程度。为了使这种自觉发展到一种进步的联合,我们需要提出“外省”这个概念,在文艺空间上呼唤一个连结的“外省地带”。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对全国腹地有普遍意义的东北,也希望看到一个与东北携手同行的广大腹地,我们将在“外省文艺”下共同团结起来。我们目睹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我们目睹了衰败的景象与被边缘化的人群,但我们更相信和企盼从中诞生的希望,更渴望从这希望中所造就的改变的力量。外省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美与生活而战吧!